前篇 相遇篇
一、
我与冥想沙盘疗法的初遇,是在三年前的秋天。那时我正在日本的东京福祉大学读心理学专业的大四,经本科的指导老师介绍,认识了同朋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大住诚教授。大住教授后来也成为了我职业生涯中重要的恩师。
初次见面,大住教授表现得非常亲切热情,甚至带着几分强硬。他一脸神秘地问我:“你知道冥想沙盘吗?”
听到这个问题,我是有点懵的。我知道冥想,正念疗法里这方面的介绍很多,我也知道沙盘,本科的指导老师就是沙盘流派的,经过这几年的熏陶我自认为对此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但“冥想沙盘”又是什么呢?一边冥想一边摆沙盘吗?可是冥想不是要闭眼的吗?闭着眼又要怎么摆沙盘?一瞬间我脑子里冒出了一连串的问号,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教授,我不知道。
教授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外或者失望,而是依旧兴致很高地开始翻箱倒柜,然后塞给我一本专业书:“这本书就送给你了,你回去好好读一读,两个星期以后再来找我,我让你亲身体验一下冥想沙盘疗法。”
我很想告诉他我还没有答应要来,请不要说得好像已经定下了一样,但想了想还是作罢了。日本大学的大四没有实习,大家都在为求职活动四处奔走,而我最初就打算回国发展,所以除了毕业论文以外也没什么其他事情可做,意外地清闲。既然闲着也是闲着,那体验一下新奇的疗法好像也不错。加上教授二话不说送了我一本价值不菲的专业书(日本这类书通常在人民币150元以上),再拒接未免有些难看了。我就这样半推半就地答应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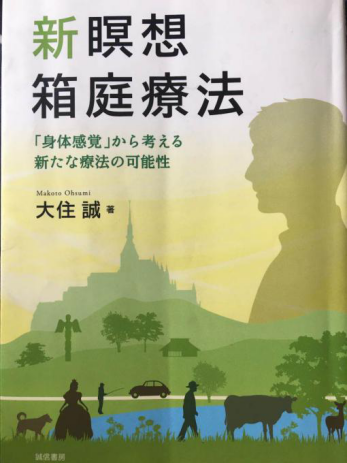
(日文中沙盘被称为“箱庭”)
回到家以后,我一边想着“这还真是一位奇特的教授”,一边读起了这本书。书是大住诚教授自己的著作,专门介绍冥想沙盘疗法的。仔细研究了一下这种疗法的实施方法,我发现所谓的冥想沙盘是要让治疗者和来访者一同冥想一段时间,然后治疗者继续闭目冥想,来访者起身独自去制作沙盘。等沙盘制作完毕以后再由来访者将治疗者叫起来,两人一同去看沙盘作品。而且,这种疗法的理论核心既不是正念疗法也不是传统沙盘疗法,而是日本的本土疗法——由森田正马所创的森田疗法。也就是说,这种疗法中糅合了冥想、沙盘疗法和森田疗法三种成分,看起来非常的混乱,让人抓不住头绪。
我不禁腹诽,心理疗法这种东西又不是简单地把所有有效的东西杂糅到一起就能更有效的,一般的做法都是在一种基本流派的基础上进行小幅度改良,把两种流派结合到一起就已经顶天了,这三种疗法的结合,也太夸张了吧?
不但如此,还有更致命的一点是,关于“这种疗法究竟是基于什么原理产生效果的”这一部分,我看不懂。这种不懂不是语言能力的问题,而是因为这部分内容过于“玄妙”,与我大学四年所学的所有心理学理论都不一样,没有严谨缜密的理论逻辑,而是不断在强调一种“感觉”。此外,还有大量的篇幅在讲述日本佛教的“禅学”,用词极为生涩,就算读懂了字面意思,也完全弄不清这其中想表达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因此,我很快对这本书失去了兴趣,只读了一小半便扔到一边,在这两个星期里再也没有想起过它。
二、
两周后,我如约又去见了一次大住教授。他依旧很热情,上来就问我:“书看得怎么样了?”我有些心虚,但为了表示自己不是一无所知,便谈起了还勉强记得的疗法实施流程。教授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只看了一个皮毛,而是很高兴地说:“对!就是这样!”后来话锋一转,他这样问我:“徐同学,你是中国人,你知道‘道’是什么吗?就是老子庄子所说的‘道’。”
这还真是一个极为哲学的问题。别说大多数中国人对于道家思想都只是一知半解,就算对此深有研究的学者只怕也不敢肯定地说自己完全了解“道”这个终极概念的真意。我也只能保守地说:“稍微知道一点点。”教授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可能是因为他之前问过的日本学生甚至业界学者都全部回答“完全不知道”的缘故吧。他说:“‘道’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概念,也有很多种解释方式,但在我的理解里,‘道’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其实他在说这一段话的时候用了很多的比喻,形容这是一种“与周围的环境、空间融为一体”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自我会扩散开,人会忘了自己的存在,就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他还写了“坐忘”这两个汉字给我看,很努力地希望我能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不过这些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理解起来没什么困难。“天人合一”“坐忘无我”,这两个词就足以说明一切。
只是,这种玄之又玄的概念一般只会出现在各种武侠或者玄幻的小说中,我实在是想不出这些与眼前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与科学的心理疗法又有什么关系。对此,教授告诉我:“因为冥想沙盘中的冥想并不是正念的冥想,而是道家的‘坐忘无我’,追求的就是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所以,让我换一种比较贴切易懂的说法。接下来我即将要体验的其实是,“打坐”?
我带着无数的问号跟着教授去了隔壁的沙盘室。幸好,那里并没有摆着蒲团,也没有供奉三清像。它看上去只是一间很普通的沙盘室,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简陋的。玩具的数量很有限,只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半人高的小架子,放不下的玩具还蔓延到了旁边的桌子上,显得不太正规。唯一有点特别的是两个呈45°摆放的黑色单人小沙发是背对着沙盘盒的,离外墙不算远,面对着一扇小窗户。但尴尬的是窗户高了些,沙发矮了些,于是坐下来的时候我的视线前方完全是白色的窗台,没办法看到窗外的任何风景。就算抬起头,也只能透过窗户看到一小部分天空而已。(与这间咨询室相比,我现在所在的咨询室简直太理想了。)

三、
在沙发上坐下以后,教授指导了我一下冥想的技巧:“把意识轻轻地放在呼吸上,脑袋放空,如果有杂念的话,不要深想,让它轻轻地流走。等我告诉你‘可以去做沙盘了’的时候,你就起身去自由地制作沙盘,等做完了再来叫我。”我一边记下,一边暗想原来教授也是很普通地坐在沙发上啊,不需要盘着腿坐。(但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天真了,教授后来经常会脱下脱鞋,盘腿坐在沙发上冥想。选什么姿势完全凭当时的心情。)
开始冥想以后,我感觉这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的。因为我从小开始就是个脑袋停不下来的人,总会不停地去思考一些什么,甚至同时去想两三件事,脑袋放空的感觉几乎从未体验过,我也不认为自己马上就能在这里做到。果然如我所料,冥想的这十分钟里我脑中的各种有的没的想法完全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能做到的只有不断告诉自己放松,以及不停地打断那些不小心想得太深的内容。至于什么“坐忘无我”,更是提都不要提了。杂念都没有停过,“忘我”自然也无从谈起。到了教授叫我起来做沙盘的死后,我连一点放松的感觉都没产生。
沙盘我原来是体验过的。在大二的时候,指导老师让学生一个一个到沙盘室去进行过一次沙盘实践,而且是以一对一的形式,在不被打扰的环境中完成的。当时的作品里有大片的蓝色,摆放的玩具也缤纷多样,自我感觉还是玩得比较尽兴的。

(大二时的沙盘作品)
所以这一次制作沙盘的时候,我也比较驾轻就熟,知道该注意的是什么。不去提前构思要如何去做,而是起身以后在面对沙具架时凭感觉行事,看中什么就拿什么,摆哪里舒服就摆哪里。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沙盘盒中得到更好的表现。记得当初第一次做的时候我还纠结了挺长时间要怎么摆,这一次却好像没怎么犹豫,随便拿了几个大体积的玩具往中心和四角一摆,完美,看着就舒服了。

(这一次的沙盘作品)
不过,就算在这一次制作沙盘的时候,我对于沙盘象征意义的了解依旧还是太少了,不明白自己的作品究竟代表了什么。时至今日回头看一看,这个作品呈治愈性的曼陀罗构图(中心明确,周围呈规则的同心圆或方形的布局),而且中央的巨树充满了大量的生命力量。出现这种作品意味着我的精神状态将会出现治愈性的阶段转折。与前次的沙盘作品对比一下,这一次的作品中没有太多个人意识的干扰(由经验或理性形成的个人审美等),呈现出了我内心中更原始更深层的部分。而这完全是之前那几分钟冥想的效果,哪怕我个人感觉状态很差,结果也清晰地体现在了沙盘作品之中。当然这些事情,我在制作的当时是一无所知的。
我把教授叫起来,两人一起围着作品看。我本以为他会向我解释一些什么,比如象征意义,或构图布局之类的,但他完全没有提及。他只问我:“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比如,有没有觉得周围的颜色变得更鲜艳了?或者房间里的空气感觉变得不一样了?”但我在这方面实在是个很迟钝的人,简单来说就是“难以发现世界之美”。我也没有刻意去迎合教授的话,而是极为坦诚地告诉他:“没有,我什么也没感觉出来。”
教授并没有失望,看上去不以为意,只是跟我说:“那你两周后再来吧。”我忍不住问他:“这个作品有什么意义吗?”他回答说:“我这里不会具体解释的,解释了反而会减弱效果。我们两周后再见吧。”
就这样,我的第一次体验在这种不明不白的状态下结束了,还被强硬地约了第二次。回家的路上,我也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心情。感觉好像这次体验什么都没得到,没感觉,没状态,没解释。如果不是因为真的比较清闲,我一定会认真地拒绝掉第二次体验。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依旧没有去看那本书。
四、
在约定的日子的前一天晚上,我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我的一个相熟的读初三的小网友对我哭诉,她因为考试成绩退步了一点而被母亲歇斯底里地揍了一整个晚上。被抓着头发往墙上撞了几十次,而且被骂了很多非常可怕的话。我为她的遭遇而颤抖,但隔着屏幕,面对着无数无法改变的现实问题,我就算是心理专业的准从业者,能做到的事也太少太少了。这一点其实就算是已经正式从业的现在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我的战场是我的咨询室,但是对于那些连咨询室都到达不了的人,甚至连稳定视频都无法保证的人,我只能哀叹他们的处境,却很多时候有心无力。
那一晚我也是如此,而且我因为自身的不成熟,严重地被她的情绪卷了进去,自己也陷入了一种相当可怕的情绪之中。这种情绪让我几乎无法入睡,睡着之后全是噩梦,就算第二天醒来以后也无法平静。在骑着自行车前往大住教授所在的大学的路上,黑色的情绪在我心中不断地翻滚,负面的想法一个接着一个,我无法让我的这些想法停止,也无法抑制住我心中的涌出的巨大的愤怒。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冥想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但脑中却像正在经历暴风雨一样,惊涛骇浪。我甚至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剧烈跳动所发出的声音。
做沙盘的时候,我依旧把自己交给了当场的感觉。一边拿玩具我一边自嘲:“哎呀,这次的心理状态可挺糟的。”

(第二次沙盘作品)
巨大的火焰、恶鬼、墓地、面目狰狞的鬼楼、血池、火山、海啸。就算我再怎么不了解沙盘的象征意义,也能轻易地明白这一幅“地狱图”完全是我内心愤怒情绪的体现。
我问教授:“这次是不是很糟?”他回答我:“不,它很好地体现了你的内心。你现在感觉有什么变化吗?”我依旧很坦诚地回答:“没有。”“那两周后再来吧。”
虽然我当时回答了“没感觉到变化”,也的确是这样感觉的,但在十几分钟后,在回程的路上即将到家的时候,我突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在回程的这一路上,那些几乎占据了我整个意识的巨大的愤怒和那些负面的想法,再也没出现了。我感到了安宁,身子还有了一些余力,去看了看开在路边的小花都是什么颜色的。这些在我前往大学的那一路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有点不可思议。
回家以后的某天,我与合租的室友闲谈的时候她问了我一句:“你的抑郁最近怎么样了?”
是的,我本身是有些抑郁的。可能与长年的留学生活过于孤独有关,可能与文化差异导致的慢性压力有关,也可能与我当时恋爱受挫、刚刚分手有关。总之,那段时期我的精神状态其实是相当差的。常常一整天陷入无法动弹的极度消沉的状态,饿得不行了才会比自己去做饭,然后一边看着锅里的开水在翻滚,一边被莫名的悲伤袭击,开始没有理由的痛哭。我不止一次在卧室、在厨房、在浴室痛哭着缩成一团蹲在地上,也不止一次想过要不要去找自己导师或者专业的医生开点抗抑郁的药物,那可能会让自己能稍微舒服一点。
这些室友多少也知道一些,所以她关心地问我,“最近怎么样了”。我愣了一下,想了一会儿才回答她说:“最近没再犯过了。”也正是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很久都没有抑郁发作过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仔细地向前回溯,想了很久。
好像是,三个星期前。
那正是,我第一次做完冥想沙盘的时候,而且除此以外,我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任何稍显特殊的事情。
我想,我真正与冥想沙盘疗法结缘,正是在这一刻吧。我可能就是在这一刻下定了决心,要在无数心理疗法的流派中选择这一种由大住老师独创的、名不见经传的冷门疗法,并决定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将其贯彻始终。

